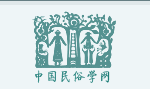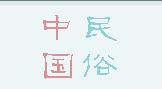|
摘 要:黄飞鸿电影系列中的民俗元素,作为文化记忆载体,随着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变动而经历了从具象到抽象的变化,体现了制作者和观众的文化认同。1950与60年代的早期作品中,围绕着市井武师黄飞鸿有大量具体而精确的民俗描写,体现了制作者和观众之间的文化默契;1970年代,随着香港文化的形成,建立在广东文化基础上的民俗从黄飞鸿电影中消失;1990年代后制作的黄飞鸿电影则将民俗抽象化,消解了黄飞鸿与乡土的文化联系,使其实现了从市井武师到民族英雄的转化,完成了记忆的重新建构,又在电影的影响下反过来建构新的“传统”。
关键词:黄飞鸿电影;民俗元素;民俗主义;记忆建构
以广东拳师黄飞鸿为男主人公的黄飞鸿电影诞生于1949年,到1997年为止共制作发行作品100部。在这近50年间里,原本只是一名普通市井拳师的黄飞鸿先是被塑造为代表武术家理想形象的儒侠,成为1950与60年代普通香港人心目中的英雄,到走下神坛几乎被遗忘,再到1990年代以青年侠士、民族英雄的形象重生,在银幕上经过了多次的形象转变。作为电影作品,黄飞鸿系列一直属于商业影片的范畴,是典型的通俗文化产品。香港电影研究者钟宝贤把黄飞鸿电影称作“港粤色彩南方电影”的代表,蒲锋也指出早期的黄飞鸿电影中充满了广东风情。对香港武侠片具有深远影响的导演张彻虽未直指黄飞鸿系列,但也隐约对其时的武侠电影给予了“香港街坊风味”“广东街坊风情”“老土”的评价。这些色彩和风情来自影片中随处可见的大量民俗元素,除颇具代表性的广东醒狮外,还有粤曲、小调、诞会等。
电影中的民俗元素,未必就是由该民俗的传承者集体创造、传承和享用的生活文化本身。更多时候,民俗在电影中只是作为一种“可用的财富”被加以商业化利用。但是,黄飞鸿电影作为举世罕有的长寿电影系列,其中民俗元素不仅仅是艺术表现手段,而是作为文化记忆的载体,体现了电影制作者和观众的文化认同。本文将从民俗主义的角度,对黄飞鸿电影中的民俗元素的记忆建构作用进行考察,以究明其变化的社会和文化轨迹。
一、香港银幕上的“广州人”
黄飞鸿出生于南海西樵,扬名于香港的大银幕。他自少年时起随父亲黄麒英辗转广州和佛山以卖武为生,20岁前后被广州铜铁行聘为教头开馆授徒,1925年在广州去世。在其70余岁的人生中,广州一直是他的主要活动区域,因黄飞鸿电影而名震天下的宝芝林药局也在广州。因此,黄飞鸿和当时大多数从周边乡镇涌入省城并落地生根的外来人一样,本质上是一个广州人。这个“广州人”的身份,在1950、60年代关德兴主演的早期黄飞鸿电影中,一直是非常明确而具体的。
首先敏锐地发现这一点的是蒲锋。正如蒲锋所言,这一时期的黄飞鸿电影对广州的执着,仅在片名上就得到了充分地体现。到1968年《黄飞鸿威震五羊城》为止的67部黄飞鸿电影中,直接出现广州地名的就有15部,其中不乏“观音山”等如今在广州年轻一辈中已鲜有人知的地名。在影视作品中以地名明确故事的地域背景,显然并不少见。黄飞鸿电影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影片制作地在香港而故事发生地在广州,而且在于作品细节对广州人文、地理和普通民众生活习俗不厌其烦的精确表现。换言之,影片中的民俗元素无论是形式、流传区域还是传承者的社会属性,都非常具象。
以1957年的《黄飞鸿狮王争霸》为例。影片多次出现早期黄飞鸿电影几乎不可或缺的饮茶场面,烧卖、叉烧包等代表性的广式点心名称不绝于目,伙计肩搭毛巾、手提大水壶穿梭于茶客之间。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黄飞鸿电影剧本和表演都相当粗糙,多有充满生活气息但与故事情节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相较之下,本片无论情节还是对白,都可谓相当紧凑。但是,在其中一个承运商把药材提货单交给老主顾黄飞鸿的场景中,仍然就货船的行驶路线作了并不直接推动情节的说明,即该船先停靠花地码头,后到西门口,最后才到沙基码头,并建议黄飞鸿到沙基码头去提货,因此处离宝芝林最近,最为便利。其后,又安排了一个船先到“大钟楼”报关稍后才到的情节,使提货遭到延宕,为后面的矛盾冲突埋下了伏笔。以一条行船线路将这四个地名串联起来,非对广州的航运以及街道、河涌分布了如指掌是做不到的,而要理解这样的线路安排,则至少必须对广州有相当的了解。也就是说,这一细节的存在意义是建立在制作者和观众拥有共同知识背景的基础上的。此外,由于狮王争霸发生在金花娘娘诞会,这部总片长不足90分钟的作品里,用近10分钟对诞会风俗进行了细致的铺陈,包括通过人物对话介绍诞会陈设及其作用,醒狮朝贺,当地年轻未婚女性以“金花契女(干女儿)”的身份行辟邪之礼,由其中人物优秀者为金花娘娘簪花挂红等风俗。加上前面穿插在其他情节中的父老代表在各商号筹措打金花的款项、到十三行打金花、“金花契女”们相约置装赴会等情节,几乎可以作为一个完整的金花娘娘诞民俗调查记录。由于金花庙在珠江南岸,广州人俗称河南,因此该地名在片中多次出现,并经常作为与河北(珠江以北的广州城区)相对的地区概念,在推动戏剧冲突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将珠江南北称为“河南”“河北”,与称江边为“海皮”一样,都属于广州特有的民俗语言,而南北两岸居民之间既不可分割又不无隔阂的微妙关系,这是连现在广州的年轻人也很难准确捕捉的民俗心理。
如果说航道设计作为民俗现象不够典型,而金花诞作为广泛分布于粤语方言区(包括香港)的非日常民俗又过于典型,那么在此片中多次出现的娥姐粉果,作为日常饮食民俗则无疑是本文更加恰当的讨论对象。先看看卖粉果的娥姐所唱的一段粤语小调:
请你大家行匀全城
欢记第一粉果出名
香夹滑兼甜甘皮爽价公道最平
河南河北有啲惯熟人
搭船来定
日日唔够应市
帮衬就快啲开声
好似大家斗抢斗得来势擒擒青嗻
人人话靓粉果的确靓
包你食咗肥兼有福
艳福齐天运气亨通去赌实会赢
唔止本处啲客话靓噃
琼崖南海顺德啲客都话我啲粉质靓
麻油肥膏上等净粉
五花瘦肉靓剥壳虾嫩鲜肉笋
馅香够味皮薄夹干净
为卖大包本都不计
用足材料靓嘅噃
呢呢呢食一件呢肥一年
呢食多件呢肥几年
係买快啲趁今日咁平
再看看《岭南民俗事典》中的“娥姐粉果”条:
粉果原是民间美食。《广东新语》有云:“平常则作粉果,以白米浸至半月,入白粳饭其中,乃舂为粉,以猪脂润之,鲜明而薄以为外,荼蘼露、竹胎(笋)、肉粒、鹅膏其中以为内”,“名曰粉果”。
娥姐是20世纪初广州茶香室的一位女点心师,貌美,她所制的粉果特别精细可口,人们乃以娥姐粉果称之。现此品仍沿用传统制法,以饭粉为皮,馅有猪肉、生熟虾肉、叉烧、笋肉、冬菇等,更为精美。
粉果非广州独有,但粉果冠以“娥姐”之名,则必为广州独有。为使人物关系和剧情更加紧凑,片中的娥姐被安排成鬼脚七表叔的女儿,由于人才出众,在诞会上代表河南的金花契女为金花娘娘簪花挂红,茶香室也被改为位于金花庙斜对面的欢记。即使人物背景有这些改动,但粉果应有的“麻油肥膏上等净粉,五花瘦肉靓剥壳虾嫩鲜肉笋,馅香够味皮薄夹干净”,以及闻名遐迩、一座难求的品牌效应都表现得极为具体而真切。
除为适应电影表现手法略为美化外,将广州和广东民俗现象几乎原状照搬放上银幕情况,还见于其他早期黄飞鸿电影,如1955年的《黄飞鸿花地抢炮》中的抢花炮,1956年《黄飞鸿义救龙母庙》中的龙母庙摸龙床、坐龙床等习俗。
纵观整个黄飞鸿电影的历史,广东醒狮是其中至为重要的民俗元素之一。据统计,约四分之一的黄飞鸿电影有舞狮场面。舞狮本身就具有极强的表演性,因此,早期黄飞鸿电影中的醒狮场面基本上是现实中醒狮表演的忠实再现,除少数需要切入人物表情和对话之处外,基本上是采用单一固定机位拍摄,并从头到尾放一遍。不排除这样做是因为当时的香港粤语电影不支持复杂、细致的制作方式,但更多是电影制作者有意追求的结果。醒狮作为广东武馆的门面,舞狮几乎是习武者的必修课。早期黄飞鸿系列的重要演员皆有南派武术功底,其中林世荣的扮演者刘湛是黄飞鸿徒孙,大多数龙套演员则皆是黄飞鸿的直系弟子,尤以刘湛及其子刘家良所率刘家班成员为多。从第一部起执导了绝大多数黄飞鸿电影的导演胡鹏在其回忆录中,曾不无自豪地写道:
本片(《黄飞鸿长堤歼霸》,1955)有一幕醒狮会金龙的大场面,和醒狮采青。
说起“采青”,是广东武馆一项极富艺术性的传统功夫,所采的青,种类繁多,有艺高人胆大在竹竿上所采的高青,有百发百中的飞铊采青,而在本片所采的“蟹青”,是考验采青者的臂力,腰力和腿力的高难度动作。
监制曹达华,刻意安排演出几场醒狮采青罕有的狮艺功夫,特别请商黄师傅唯一女弟子邓秀琼女士和她的公子吴殷志,双双表演醒狮采青的精彩项目,计有“狮子过三山”、“盘青”、“凳青”、“睡佛采灵芝”等,均由刘湛师傅亲自掌鼓,陈耀林师傅舞大头佛,这些都是一生难得一见的精彩演出,难怪影迷大饱眼福。
不仅如此,多部影片中代表宝芝林在重要场合舞狮头的皆是刘湛扮演的林世荣,而曹达华扮演的首徒梁宽则持棍站在路边负责护卫。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朱愚斋的小说里,这种情况都是不可能发生的。显而易见,醒狮表演在早期黄飞鸿电影中并非推动或构成情节的手段,表演精彩的、地道的醒狮本身就是目的。这些设计,无疑建立在导演和演员都对醒狮非常了解的基础上,胡鹏断定影迷也因此大饱眼福,可见他显然相信观众对醒狮的了解程度与自己不相上下。事实上,这种文化上的默契正是早期黄飞鸿电影中民俗元素运用的特点。
1950年代对香港的普通华人来说,是一个重新定位政治身份的年代。广东民间至今有“广州城,香港地,澳门街”的说法,当时广州作为府城,无论文化、政治还是经济地位都远在港澳等地以上,对省港澳三地居民来说是无可取代的中心。粤港由于土地相连,方言相同,虽然分别在不同政府治下,但一直可以自由往来,地缘关系极为密切。每逢天灾或经济、政治危机,往往会有大量广东居民走避香港,有的定居下来,大多则待危机过后重回故里。其时,由黄飞鸿等武师构成的所谓广东武术界,本质上是由在城市中谋生的劳动者结成的广域互助网络,覆盖省港澳及佛山等地,人员在此数地间流动并不鲜见。关德兴等人所在的粤剧界则一直穗港并重,规模完备的大戏班称为“省港大班”,常年游走于粤港澳湛及海外华人社区。1940年代末内战激化,战火南移,大量难民涌入局势相对稳定的香港。但是,随着1951年大陆关闭深圳边境,这些难民没能像过去那样待局势好转便回归故里,而是被留在了香港,而1949年8月生效的《人口登记条例》则规定所有香港境内居民均须登记并领取身份证。不管情愿与否,这些来自广东各地、以广州作为文化认同指向的人们,就此落地生根成为香港人。
这种情况显然符合科斯特林所说的因社会变动等所产生的集体焦虑,而民俗主义即是治疗或补偿这种焦虑的手段,起到了对经济、文化、社会变动或沟通条件变化中产生的文化断裂进行弥合或联结的作用。在社会变动中,受到地域性、历史性或功能性压迫的“传统”,会根据不同的目的建构“外向型”的民俗,亦即具有较强的向外展示特性的“片断化文化”,如民俗服装、民俗习惯、民谣、民俗舞蹈等以“观众”的存在为前提的文化,并以适当的方式呈现出来。
但是,对早期黄飞鸿电影的制作者和观众的情况进行考察,则似乎情况有明显不同。实际上,香港虽然在移民的意识里只是暂居之地,不得不被困于此,但此地对他们来说毕竟不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不仅文化上与广州具有很大的同质性,而且过去就一直是他们安家和谋生的选择之一。也就是说,他们重新定位的只是政治身份,文化身份并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他们仍然是影片中的民俗的传承者。即使像娥姐粉果这样的地方小吃被留在边境线的那一边,他们对它的喜爱和向往依然鲜活,依然以记忆的方式享用着这些物理空间上已经远离的民俗。这正是黄飞鸿电影的制作者和观众间文化默契的由来。电影中的民俗只要具体、精确地呈现出来即可,不需要向观众作解释,观众自然能够理解。他们会随着影片如临其境地参加一次金花娘娘诞会,听到娥姐边卖粉果边唱的小调仿佛就能尝到刚出笼的粉果丰腴鲜美的滋味,从醒狮朝贺的礼仪和采青技艺就能一眼看出舞者功夫的好坏。这些民俗现象与对白中大量的俚语俗话、机锋语、客套话等,共同组成片中人物完整的活动环境,同时也是他们所熟悉的、在文化心理上最为舒适的生活世界。因此,电影中的民俗元素不是被建构的“外向型”“表演性”的民俗,而是内向的、分享的,制作者和观众是“自己人”,有着共同的文化记忆。
蒲锋强调了这种“自己人之间的分享关系”,称黄飞鸿电影是“一群广东移民拍给广东移民看的”,其中“丰富的广州府细节,正帮助他们缅怀那个失落了的世界———广州”。在没有足够史料支持的情况下,无法揣测观众的情绪,只能说他们与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文化认同。早期黄飞鸿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南北对比,也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在《黄飞鸿官山大贺寿》(1956)中,反派借以掩护对黄飞鸿进行偷袭的是一头造型丑陋的北狮,黄在打败对手后对这头北狮表现出毫不掩饰的鄙夷。前述的《黄飞鸿狮王争霸》中,娥姐在完成金花诞的簪花礼后,问刚刚成为好友的湖南船娘“你乡下有没有这些?”而对方则答以没有,“未见过”。这种“南”和“北”的相对性甚至对立性表达,其意义显然不在说明地理位置,而是一种“我”与“他者”的身份对立。尽管身在香港,具象的广州民俗是电影制作者和观众共有的文化记忆,他们的自我文化身份定位与银幕上的黄飞鸿一样,仍然是广东人,或者严格地说是广州人。
继续浏览:1 | 2 | 3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