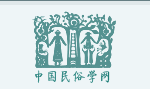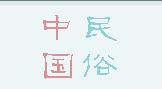|
[摘要] 国内的牛郎织女研究大约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纵观80余年学术史120余篇论文,大多乏善可陈,其种种流弊,折射出整个人文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诸多问题。诸如不尊重前人劳动成果、二手三手材料的反复转用、不合逻辑的材料堆砌、牵强附会,乃至重复操作、以讹传讹,都在牛郎织女研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从目前的资源储备与研究范式看,至少在牛郎织女研究领域,传统的历时研究已经陷入困境,资料匮乏,明显不足以支持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因此,实地的田野调查与活形态的共时研究就有了别开生面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体现为新材料的进入,也体现为研究范式的转换。
[关键词]:学术史;学术批评;天鹅处女;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研究
[作者]:施爱东,1968年生,江西信丰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学界对牛郎织女这一口头传统的归类比较复杂。几乎所有的民间文学教科书都把它列为中国的“四大传说”之一,也有学者使用广义的“故事”概念来指称,但是,大多数的目录索引却把相关研究成果归在“神话学”领域,而风俗研究则把它视为“岁时民俗”或“时间民俗”中的社区仪式或群体记忆。进入21世纪之后,许多地方文化工作者倾向于把牛郎织女口头传统看成文化事件,试图借助历史人类学方法把它落实到地方文化建设当中。
基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许多论文只好用“神话传说”“神话故事”“传说故事”这样一些互相矛盾的定性词来指称有关牛郎织女的口头传统。本文不拟武断地将它划入任何一种体裁或形式,只以“牛郎织女”作为这一口头传统的通称。
国外的牛郎织女研究开展得比较早。1886年,法国人高延(J. J. M. de Groot)就在他的Les Fêtes Annuellement Célébrées à Emoui一书中对牛郎织女与七夕风俗展开过讨论[1]。1917年,长井金风《天风姤原义(牵牛织女由来)》[2]对牛郎织女进行了专题研究。国内的牛郎织女研究起步略晚,较早的有钟敬文1925年的《陆安传说·牛郎和织女》[3]、1928年的《七夕风俗考略》[4]等,延至2008年,笔者检索到的相关论文120余篇(不含七夕风俗类专题),其中1955年范宁的《牛郎织女故事的演变》[5]是文献资料梳理较为完备的一篇,而王孝廉始发于1974年的《牵牛织女的传说》[6]、洪淑苓完成于1987年的硕士学位论文《牛郎织女研究》[7],则是集大成的研究专著。自此以降,多年不见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牛郎织女研究中表现出来的种种流弊,折射出国内人文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许多问题。
牛郎织女的起源与流变研究
1920年代以降,继顾颉刚层累造史观的提出,“演变”“演化”“演进”几乎成为知识考古话题中最热门的学术用语。起源与流变问题是20世纪牛郎织女研究中关注最多、历时最长的一项。
1929年,茅盾《中国神话研究ABC》把牛郎织女传说界定为“现所存最完整而且有趣味的星神话”,此书在简单的文献梳理之后,得出结论说:“可见牵牛与织女的故事是渐渐演化成的”,并且断定“在汉初此故事已经完备了”[8]。茅盾的主要观点与日本学者出石诚彦发表于1928年的《牵牛织女说话の考察》[9]基本一致。这一论断似乎从一开始就成为定论,尽管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精细化作业,在断代问题上也与茅盾略有出入,但主要观点并未偏离这一论断。
茅盾在该书中罗列了许多涉及牵牛与织女的材料:“(一)《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大东》;(二)古诗十九首里的《迢迢牵牛星》;(三)曹子建的《九咏》;(四)梁吴均的《续齐谐记》;(五)《风俗记》和《荆楚岁时记》;(六)《李后主诗》、《艺文类聚》所载古歌、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周密《癸辛杂识》、白居易《六帖》等。”[10]这些材料几乎全都成为后辈学者们反复引证的主要论据,甚至他对“织女又名黄姑”的论述,都被后辈学者反复征用,但是,绝大多数学者都未在文中提及“茅盾”二字。
其中被后人引证次数最多的是茅盾注明出自《荆楚岁时记》中的一段:
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织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使一年一度相会。
有趣的是,钟敬文早在发表于1928年1月的《七夕风俗考略》[11]中即已引述这个故事,注明出自《齐谐记》,并且指出:“某辞书,于七夕织女两条,都援引这故事,文字与此略同,而以为出自《荆楚岁时记》,我手头所有汉魏丛书本的《荆楚岁时记》,实无此段记载,未知其引用自何书。”
如果说钟敬文的这篇文章一般人很难找到,罗永麟始发于1958年的《试论<牛郎织女>》[12]就很容易找到。罗永麟说:“近人玄珠的《中国神话研究ABC》、范宁的《牛郎织女故事的演变》以及初中《文学》第一册《教学参考书》都注明引自《荆楚岁时记》。但查该书《汉魏丛书》、《宝颜堂秘笈》和《四部备要》各版本,均无此段文字,是传抄之误,或别有所本(逸文),尚待考证。”
孙续恩认为这段文字乃出《佩文韵府》,并且认为“《佩文韵府》所引当是佚文”[13]。我们且不说《佩文韵府》乃清代类书,核书不精、错讹杂出、删改亦多,难以为学术引证所据,就算可据引证,范宁引《荆楚岁时记》“佚文”最后一句为:“责令归河东,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与茅盾所引不合,明显多出了“七月七日”的时间节点。但这并不妨碍后来的学者继续将这段文字作为考察牛郎织女的重要材料,而且全都绕开茅盾、绕开《齐谐记》、绕开《佩文韵府》,言之凿凿注明出自《荆楚岁时记》。《荆楚岁时记》是一本常用古籍,即便如此,多数学者的研究工作亦如郑人买履,宁用二手材料,也不参考辑校本。
1979年汤池的短文《西汉石雕牵牛织女辨》[14]试图通过文献与实物的相互印证,说明现存于陕西长安县境内的“石爷”“石婆”雕像就是文献记载中的牵牛织女像。可是,两尊石像不仅雕刻风格不大一致,石质和风化程度也明显不同,甚至对于谁是石爷谁是石婆,学者们也没有统一的看法,要论证两尊石像就是汉代的牛郎织女,恐怕还有些难度。
从班固的《西都赋》、张衡的《西京赋》、潘岳的《西征赋》,以及成书于公元6世纪之前的《三辅黄图》可知,牵牛形象大约在班固时已经人格化,并有石像立于昆明池畔。但是,汤池仅仅依据《汉书·武帝纪》中一句“元狩三年……发谪吏穿昆明池”,加上后世文献中提到昆明池畔有牵牛织女像,就断定此像为元狩三年所立。也就是说,汤池已经预设了昆明池的周边设施在元狩三年到班固之间的近200年间没有任何增置,如此才能证明班固所见,即为武帝所建。
尽管汤池的结论是否可靠还有待进一步商榷,但并不妨碍这篇文章成为1980年代以来牛郎织女研究中引证率最高的论文。
值得注意的是,文献记载的石像是否留存至今,是否就是现存于长安县的两尊石雕,实在无关我们对于牛郎织女的起源研究。从文物考古的角度看,汤池的论文自有其意义,但从牛郎织女的故事发生学上看,汤池的论文丝毫无补于既有文献。石像是否留存与石像立于何时,两者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多数学者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对于论据的分辨能力不足,眉毛胡子一把抓,拿着鸡毛当令箭。
1985年孙续恩《关于“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几个问题》[15]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1、牛郎织女故事是怎样产生的?作者认为“是人与身外世界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矛盾斗争的 结果,是与原始宗教观念有密切关系的”。2、为什么选定七月七日为相会佳期?作者认为“七月七日是个吉庆日子、欢乐日子,适宜于相会的缘故”。3、为什么选定乌鹊填河?作者认为“乌鹊即喜鹊。它在古人乃至今人的心目中,是一种极笃于爱情、具有很好的建筑技能、而又能给人带来吉祥的鸟”,由于南人北人对乌鹊的看法不同,因此有了关于乌鹊好坏的不同异文。
前一个答案是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空洞答案;后两个答案则像是围绕箭头画标靶,先预设了“七月七日”和“乌鹊搭桥”是因吉祥而设,然后围绕这两件事物找理由。这样找出来的答案显然不具备排他性,比如我可以问:“正月十五(或者其他任意一个宜嫁娶的日子)也是个吉庆日子、欢乐日子,也适宜于相会,为什么相会佳期没有安排在正月十五呢?”又或者我再问:“天鹅也是一种象征爱情和吉祥的鸟,飞得极高极远,为什么没有选定天鹅来填河呢?”按作者的逻辑,根本无法应对这样的质疑。
杨旭辉的《牛女故事中鹊桥、蜘蛛意象探析》[16]就孙续恩的第三个问题进行了更细密的发挥,杨文认为使鹊为桥是因为“鹊本身具有高超的建筑本领”,它的巢又大又好,有象征家庭的意义,鹊在古代还被视作相思之鸟,后来,“鹊和鹊巢成了家庭的保护神,人们也就自然会赋予它整合家庭的功能”。
但是,宣炳善的《牛郎织女传说的鹊桥母题与乌鸦信仰的南北融合》[17]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宣炳善认为乌鹊并不专指喜鹊,而是乌鸦与喜鹊的合称,“在宋代以前的北方,乌鸦的神圣地位是任何鸟类所不能匹敌的。汉代介入牛郎织女传说的鸟,是乌鸦,而不是喜鹊。”
宣炳善由乌鸦、喜鹊在南北方地位与功能的差异,推测牛郎织女是由北向南传播的:“因为北方人在宋代以前一直是讨厌喜鹊,喜欢乌鸦的,而南方人却是喜欢喜鹊而讨厌乌鸦的。当通过移民的途径,南北文化混合的时候,乌鸦和喜鹊也就混合在一起变成一起搭桥了,统称为‘乌鹊桥’,这当然是历史的将错就错的小细节,而后来就变成了‘鹊桥’。”
宣炳善关于牛郎织女“北南传播”的路线图对我们很有启发作用,但要借助由“乌鹊桥”到“鹊桥”的变化来描绘这条路线图,证据尚嫌不足。如果说“乌”代表北,“鹊”代表南,那么,从一开始,“乌鹊”(北南)就是一起出现的,并没有一个纯粹的“乌”(北)的时期。除非宣炳善能够向我们提供一批早于“乌鹊桥”出现的、纯粹叫做“乌桥”的文本,否则,就不能强把“鹊”的时期排在“乌”之后。
2006年王帝的《牛郎织女神话传说及其演变》[18]在许多方面沿袭了孙续恩的思路,认为牛郎织女在汉代定型“有它产生的社会现实原因”:首先是当时的社会背景所决定的;其次是融入了人民最普通的生活愿望。作者由此生发说,大量的“后世文学作品”甚至如《红楼梦》金陵十二钗的女性形象都受到织女形象的深深影响。不过,作者没能为自己的这一论断提供任何直接的证据。
在述及牛的作用时,作者只是说“从男耕女织这一生活生产方式可知,他们所处的自然经济时代劳动人民对牛的依赖与崇拜。正是出于这种原因,牛被赋予了神的意义,也就具有了神性与神力。”而对鹊桥的由来,作者主要从瑞鸟崇拜的角度来谈。对于“佳期相会缘何选定为七月初七”,则通过罗列几则有关七月七日的风俗材料,得出结论说:“以上几例显示:七月七日在汉魏晋时代已形成习俗,而且均是欢乐吉祥的日子。”
这些问题和观点,许多都是孙续恩在21年前《关于“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几个问题》中已经谈及的,但是,王帝在他的“参考文献”中却只字未提及孙续恩的贡献。如果作者没读过孙续恩的论文,那就说明作者写作的前期准备不足,以至于重复劳动而不自知;如果作者读过孙续恩的论文而有意不提及,那就说明作者有待于加强学术规范的学习。
在牛郎织女的源流研究中,大量的论文只是简单重复前人已经做过的工作,如刘晓红《牛郎织女神话传说的演变》[19],从材料到观点,基本上都是前人早已述及的,此文只是做一简单复述,甚至全文“参考文献”只标注王孝廉《中国的神话世界》。
姚宝瑄发表于1985年的《<牛郎织女>传说源于昆仑神话考》,材料丰富,用力颇深,可惜作者思想过于单纯,居然把不同时代、不同源地的书面文献与口头传说视为同质时空中的系统文件。作者预设了这些文献的“系统关系”,从中精心挑选了一些略略相关的叙述进行互证,以“织女”为中心构筑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上古神话谱系。对于那些没有文献依据的命题,作者往往略去论证直接做出断语,如“天帝即黄帝,蓬莱仙人将黄帝请来作为中央天帝,后在民间演变为玉皇大帝”[20],只轻轻一句话,就把玉皇大帝定为黄帝了。此文看似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但总体上给人以刻舟求剑的感觉。
1990年赵逵夫在《论牛郎织女故事的产生与主题》[21]一文中认为,“牵牛、织女的最早命名,是指某一民族的祖先,或传说中有所发明造作的人。我认为这两个星座名,同商先公王亥及秦民族的祖先女脩有关。”作者花了许多笔墨谈论有关王亥与女脩的各种文献,惟独没有拿出证据来说明王亥与女脩如何变成了牵牛与织女,最后只以一句“当牵牛、织女作为星名被越来越普遍地接受,它们本来的含义,它们最早所具有的纪念意义,便越来越淡漠”轻轻跳过,直接把王亥、女脩与牵牛、织女对应起来。
16年后,作者在《汉水、天汉、天水——论织女传说的形成》[22]中抛弃了牵牛“王亥说”,认为“牵牛的原型来自周先民中发明了牛耕的杰出人物叔均。”而作者的论据只是“叔均发明牛耕,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海内经》。”这和作者上一篇论文仅仅依据“《世本·作篇》说:‘胲作服牛。’胲即王亥,是见之于甲骨文的殷先公。‘服牛’即可以驾耕服用的牛”立论一样,把“偶然联想”当成了“必然联系”。2007年,赵逵夫似乎又放弃了“叔均说”,认为“秦人东迁以后同周文化交融,这就造成了产生有关《牛郎织女》传说的社会与文化基础”[23]。
先秦及汉代文献中,与牛郎织女直接相关的材料极少,但是,如果不考虑直接关系,可供联想和阐发的材料又极多。于是,每变换一个联想的角度,都能找出一批可供阐发的资料,得出不同的结论。
蒋明智《“牛郎织女”传说新探》[24]从“西周时期的哲学思想、民俗风情、经济状况、婚姻形态和文学表现”等多个方面进行阐发,力证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具备了让牛郎织女结合的各种必备条件,由此推断“西周时期,就流传着织女与牛郎结为夫妻的传说”。尽管作者对上述各方面都进行了非常精细的论证,但还是给人以南辕北辙之感。一千种“可能性”论证也无法代替一种“必然性”论证,具备了生长的土壤并不意味着这棵树的存在。除非作者能找到新的更直接的出土材料,否则这一观点就很难站稳脚跟。
侯佩锋《“牛郎织女”神话与汉代婚姻》[25]认为,“牛郎织女神话在汉代的世俗演化,使这一神话传说从人物形象到故事情节再到情感内涵,都体现为一种向汉代民间世俗生活的演变。”全文比较简略,其核心论述也不够严密,比如作者借《岁时广记》卷二六引《荆楚岁时记》“尝见道书云:牵牛娶织女,取天帝二万钱下礼,久而不还,被驱在营室”,以说明“汉代嫁娶奢靡的社会风俗和择偶的种种要求在牛郎织女故事中都有所反映。”
牛郎织女研究中,引证《荆楚岁时记》的论文极多,但绝大多数学者都没有注意到《荆楚岁时记》有多种版本,更没有注意到《荆楚岁时记》载录的岁时故事均为隋初杜公瞻所注,而非宗懔原著。侯佩峰试图用隋初的牛女故事与汉代的婚姻习俗进行互证,这就颇有些关公战秦琼的味道。再退一步,即便隋初风俗与汉代风俗完全相同,“久而不还”也未必是“久而不能还”,也许是“久而不愿还”或者“久而拒不还”呢?因而也就难以用来说明“牛郎织女形象更成为汉代普通人寄托情感、消解痛苦的对象,从而使这一传说故事从真正意义上归属人民。”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文章来源:原载《文史哲》2008年04期
【本文责编:思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