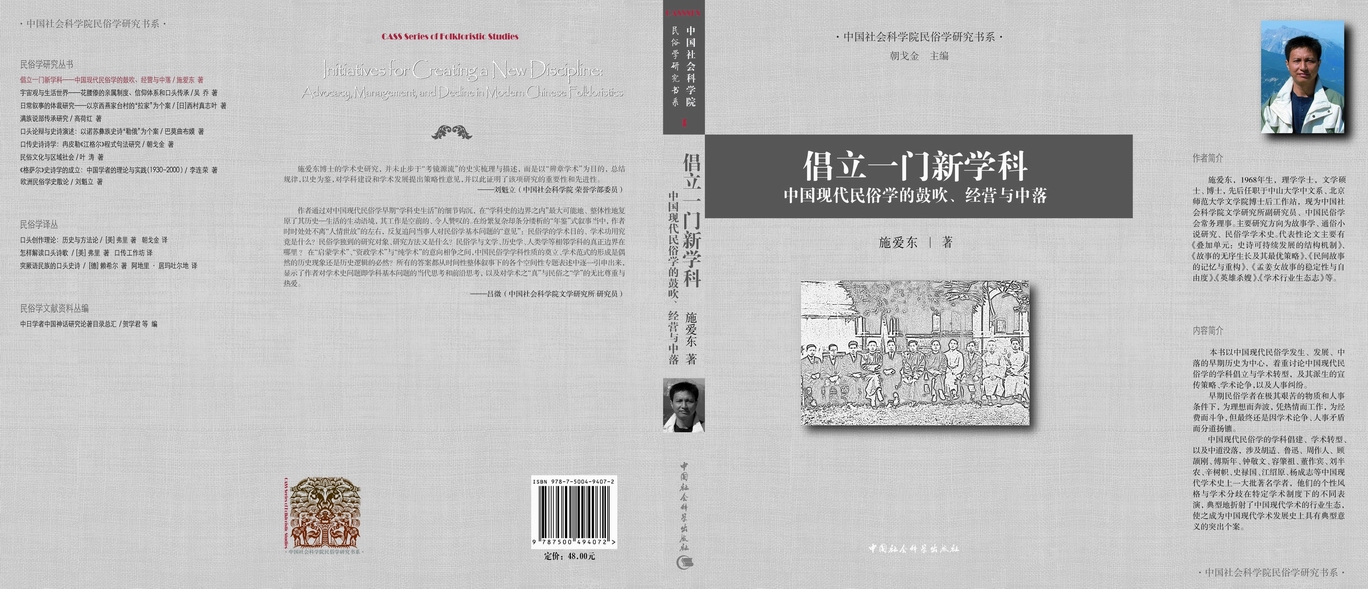

导读:学科史的边界与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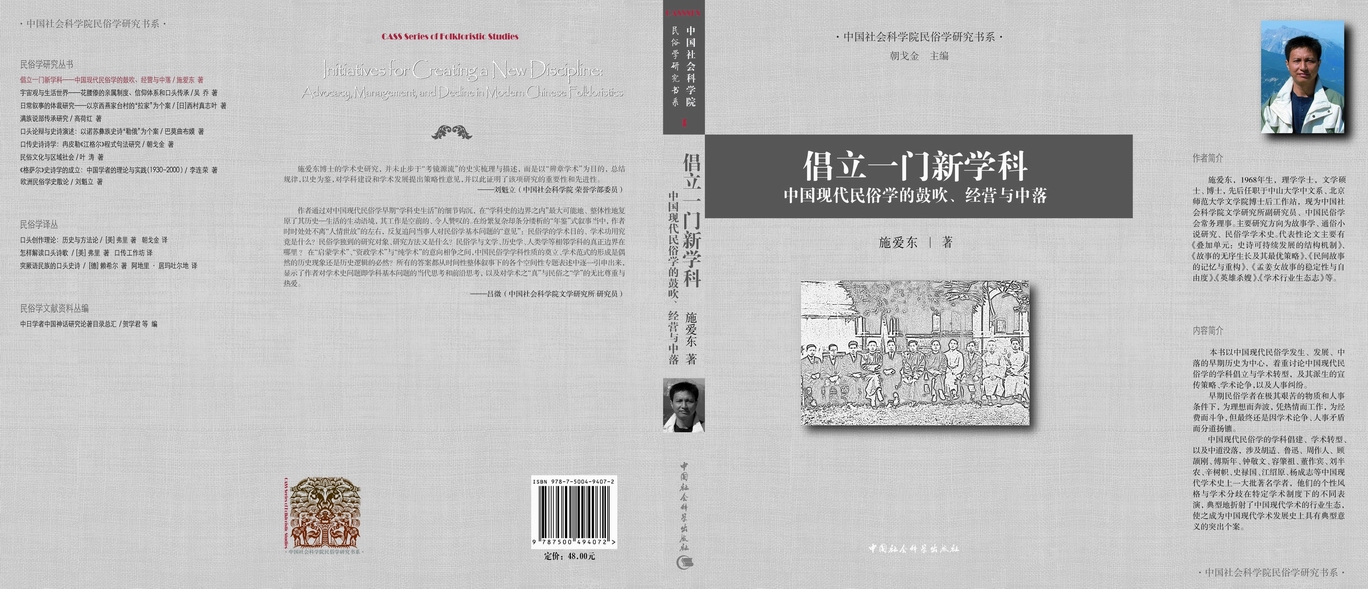

 wow,恭喜恭喜!
wow,恭喜恭喜! 




──刘魁立(中国社会科学院 荣誉学部委员)
──吕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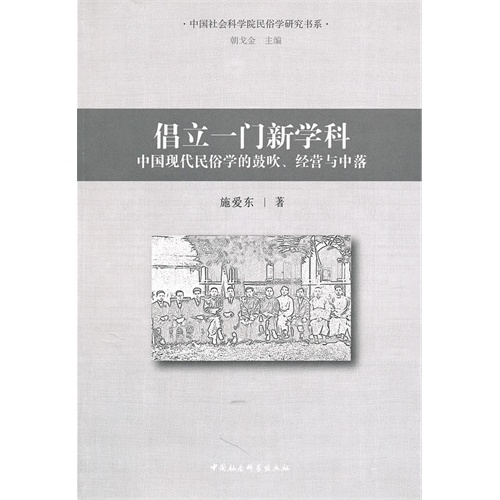

 社科院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自由,可以回家办公,不过觉得老师们都很辛苦,要不断的研究研究再研究,还要出去学习、赶场、讲学。。。。
社科院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自由,可以回家办公,不过觉得老师们都很辛苦,要不断的研究研究再研究,还要出去学习、赶场、讲学。。。。 
原帖由 施爱东 于 2011-5-13 11:04 发表社科院一般只星期二上班,而且一般只上午十点半到十二点之间在。如果没什么特别的事,一般午饭之后大家就各自回家工作去了。什么时候来了北京,可以到我们办公室喝茶,然后带你认识一下各位大佬(但不一定都在) ...
 很多学校都有自己的鬼故事的,应该不是一个人创作出来的。
很多学校都有自己的鬼故事的,应该不是一个人创作出来的。 原帖由 南池子 于 2012-8-21 21:46 发表
施老师不能对张多偏心。您给我那本书,那是作为校友,咱蹭您书。再顺带帮您稍书给刘老师他们,这是咱的半个“劳动成果”。现在多了一本,我再给多多,那是同行情谊,一下皆大欢喜。

 没捎错最好。
没捎错最好。| 欢迎光临 民俗学论坛-中国民俗学网 (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forum/) | Powered by Discuz! 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