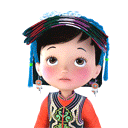古典学与口头诗学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9-02-19 00:23:27 / 个人分类:以文字为生存?
古典西学在中国:第六届开放时代论坛
昆明•2008年11月28-30日
--------------------------------------------------------------------------------
古典学与口头诗学:
在“追问”与“道路”之间反思中国人文学术的学科壁垒
(以哈佛古典学传统与中国史诗学术转型为例)
巴莫曲布嫫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
【发言要点】“荷马诸问题”的追问(zḗtēma)构成了特定的荷马学术史(Homeric scholarship)。而自亚里士多德甚或更早就开始的“追问”,可以说正是一代代学者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探求“道路”(oimai)的根本精神,也是学术研究不断得以推进、扬弃、承继、对话、磋商和发展的基本“道路”。哈佛大学的口头文学研究肇始于1856年,至上个世纪30年代前后成为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的学术重镇,经过以蔡尔德(Francis James Child)、基特里奇(George Lyman Kittredge),帕里(Milman Parry)、洛德(Albert B. Lord)和纳吉(Gregory Nagy)为代表的五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形成了逾150年的学术传统,在跨学科的国际对话中竖起了一道道探索人类表达文化之根的标杆。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北大“歌谣学运动”(1928)为其先声。本次发表难以纵论长达80年的学术流脉,现实的作为可能是在“追问”与“道路”的双向审思之中,简要回顾自章太炎开始引入的史诗概念,闻一多及其以降的史诗“缺位”迷思,文学界的史诗观形成、中国史诗传统多样性发现的学术历程;进而从“哈佛传统”(D. E. Bynum, 1974)的输入及其本土化历程,着重讨论哈佛几代古典学者的多学科视野、民族志情怀和理论性贡献,反观十多年来中国史诗学术的理念、方法与实践,提取我们朝向多学科对话的问题意识。
【录音整理】
第三场
主持人:刘小枫
发言人:巴莫曲布嫫、成官泯、韩潮、何明 评论人:张辉
刘小枫:第二场就现在开始,第二场有四位发言,第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巴莫博士,第二位是中央党校的成官泯博士,第三位是同济大学的韩潮博士,第四位是云南大学本校的何明教授。评议人是北大张辉教授。下面我们先请第一位,巴莫博士。
巴 莫:大家好! 请允许我借用一首彝族民谣来开始我的发言:天和地不相连,云彩来相连;山和谷不相连,溪水来相连;你和我不相连,一个非常好的话题──“古典西学在中国”来相连。这是彝族传统的三段诗,从天到地到人。我今天的话题为“古典学与口头诗学”,主要是以哈佛古典学传统与中国史诗学术转型为一案例来讲讲“故事”。由于学术史的跨度比较长,所以不妨采取一个倒叙的办法来“叙事”,先从中国史诗及其研究说起。
“史诗”这个词的英文epic,来自希腊语和拉丁语,从词源上来讲跟古希腊语的epos是相关的,epos的原意呢,是指“话”或“话语”,后来引申为初期的口头叙事诗,或是口头吟诵的史诗片段。“史诗”这个概念传入中国应该是在19世纪末期,那么epic这个英文概念是什么时候翻译成汉语,并用“史诗”这两个字来作表述的呢?据初步的学术史梳理(或许我们掌握的文献也还不够),现在只能说可能最早使用或较早使用的“史诗”二字的学者是章太炎。他在其《正名杂义》一文中已径直使用了“史诗”这个概念。此后,胡适曾把epic译为“故事诗”;周作人、郑振铎等也讨论过史诗。那么,到了闻一多那里,他明确指出,我们大家都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中国到底有没有自己的史诗?这样的一个争论或一种“焦虑”,一直延续到了1985年前后。实际上,在中国的学者开始谈论中国有没有史诗,或者在“焦虑”中国有没有史诗这样的一个宏大文类之前,国外、境外的中国史诗研究早就悄然勃兴了,而且成就不低。因而从学术史的发端上说,有关中国史诗的研究起步于域外,从西方关注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开始,当时进入“他者”视野的主要是蒙藏史诗。国外最早介绍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的是俄国的旅行家帕拉斯,时间是1776年。由于时间的关系,这一学术史的研究线索不能往下再讲了。
从18世纪下半叶,经19世纪,到20世纪初叶,不到两百年间,西方学者开始关注我们国家的史诗,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说文本的收集和翻译,包括研究工作,产生了一大批学者,涉及到的国家,就有法国、德国、俄罗斯、芬兰、英国等等。从境内来讲,我们的史诗研究端倪大概可以上溯到几百年前,也就是1779年,青海的一位高僧在与六世班禅通信时谈到过藏族史诗《格萨尔》,当然那不能算是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史诗研究。国内的学者最早发表文章谈论史诗的当属任乃强先生,1929年他到康巴藏区考察,1930年在《四川日报》副刊上发表了关于藏族史诗《格萨尔》的一些评述。公允地说,这也算不上是科学意义上的史诗研究。
中国大规模的史诗收集整理工作,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其间几经沉浮,到80年代学者们才大致地厘清了各民族史诗的主要文本和流布状况,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我国流存着非常丰富的史诗传统。据不完全的统计,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史诗大约有上千种,这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数字。比如说,突厥语族中的几个民族所传承的史诗就有几百种,那么蒙古族的史诗呢,据我们所一位老学者仁钦道尔吉的统计就有三百多种,这仅仅只是说到北方的蒙古族和突厥语族诸民族。南方少数民族的史诗则更多,难以计数。南北方的史诗加起来应该是不下于一千种(我们只能讲“种”,不能论“部”)。较为系统的史诗研究是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初具规模,主要以“中国史诗研究丛书”的陆续出版为标志。我们所的史诗学者朝戈金对此有个概括:这个时期的中国史诗研究从主体上就出现了一种转向,由“他者叙事”转向了“自我阐释”,因为原来主要是国外的史诗学者或者东方学学者在研究。我想所谓“转向”主要有几点:第一,我们从文类的界定上丰富了西方关于史诗在文类上的界定。原来西方主要是以荷马史诗为圭臬,以黑格尔的史诗观,包括一些经典作家关于史诗的定义,这样的一些尺度为标准。但是到国内的发掘工作告一段落以后,从类型上讲,除了英雄史诗,我们还有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今天在云大应该指出的是,迁徙史诗这一亚类型最初正是由云南学者提出来的。可以认为,这些本土的史诗类型丰富了世界史诗的宝库。第二,在传播的形态方面,我们逐步突破了经典作品或者书面史诗的文本局限,将视野投向了民俗生活,也就投向了文本赖以存在和传播的语境。第三,在传承人的分类上,我们知道西方史诗,比如说荷马史诗,俨然是早已失去了声音的文本,而我们还保有活形态的传承,所以在传承人分类上,也突破了“游吟诗人”这样一种僵固而单一的概念,比如说,我们从本土特定的文化语境去考察歌手的传承方式,以藏族的史诗歌手为例,仅传承方式就有五种,也就是说有五种类型,包括比较神秘的“托梦神授”,这一现象其实到现在也没法解释清楚;还有掘藏艺人、吟诵艺人、圆光艺人和闻知艺人,这些艺人类型从史诗的传承方式来说都是非常独特的。因此,可以说,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史诗研究格局的形成期,通常按地域把史诗传统分成南北两大系统,北方基本上是英雄史诗,南方主要是西南这一片区,则以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见长,尤其是迁徙史诗在哈尼、拉祜还有彝这些彝语支民族中是有相同的叙事程式的,比如说跟谱系,跟民族起源,跟整个迁徙路上的英雄祖先是密切相连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学术格局基本上形成,主要取决于多民族史诗传统及其多样性的“发现”,但是应该说,北方史诗的研究力量和学术成果要大大的超出南方史诗。
现在我们转接到古典学与口头诗学之间的学术关联上来谈谈中国史诗学的发展和学术转型。在我提交的发言大纲中说到“哈佛传统”(D. E. Bynum, 1974)影响了我们的史诗研究格局,为什么这么提呢?这里我想讲一个“西学东渐”的过程,尽管发生的时期相当晚近,却也说明了“古典学在中国”的一种当代走向。1995年,我们所的一位学者[尹虎彬]到了哈佛燕京学社,今天在座的有好几位也是从哈佛燕京回来的。正是在哈佛,他接触到了那里的口头传统研究,随后将一些主要的学术理念和成果译介过来。第二年,也就是1996年,我们所又去了一位学者[朝戈金],这位学者本身就是研究蒙古族史诗的,他也开始做译介工作,汲纳哈佛的口头诗学理论,回国后将之运用到了自己的田野研究中。此后,我们所还有多位学者先后到哈佛访学……这样我们所从1995年开始就陆续地把哈佛几代古典学者维系的口头传统研究及其理论和方法论成果陆续地译介到了大陆,在国内学界率先提出“口头传统”这样的一个研究领域,建立了研究中心,并在中国史诗研究中开始了口头诗学的本土化实践。
这里,就有必要回溯一下哈佛的古典学与口头诗学传统。大家都知道,哈佛既是古典学的一个重镇,同时也是美国民俗学的一个摇篮。哈佛大学的口头文学研究肇始于1856年,至上个世纪30年代前后成为口头诗学(Oral Poetics)的学术旗舰,其间经历了以蔡尔德(Francis James Child)、基特里奇(George Lyman Kittredge),帕里(Milman Parry)、洛德(Albert B. Lord)和格雷戈里·纳吉(Gregory Nagy)为代表的五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形成了逾150年的学术传统。蔡尔德原为数学家,后来转行成了修辞学和演说术讲席教授。他曾任“The British Poets”的总编辑;主要是搜集和研究英格兰和苏格兰民谣,目的是在言语与书写之间探究思想表达的基本差异,这也构成其毕生的追问。他编辑和出版的English and Scottish Ballads影响深远。哈佛最早的“口头传承特藏”(The Folklore Collection)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收藏了7000册多语种的口头文学文本,含民谣、民歌和故事,其中包括若干19世纪的珍贵资料。需要说明的是,当时以至后来,Folklore这个词在西方,包括美国和欧洲主要是指“口头传承”,不是我们大陆现在理解的“民俗”。1856年,蔡尔德编辑的第二卷“The British Poets”收录了300首英格兰和苏格兰民谣,哈佛口头传统研究的始端,也就从这一年算起的。他的学生基特里奇,早年与老师一道进行口头文学收集、出版、公众教育和图书馆改进等工作,是英语系的教授;他毕生继承老师的衣钵,并且极大地拓展了原有的资料搜集范围和研究领域。早年在口头文类方面,他收集了民谣、民歌、故事、谚语,乃至巫术信仰的历史等,地理范围从英国、欧洲到美洲大陆。当时他的学术兴趣主要是与口头传统相关的古代和中世纪文学,包括奥维德的《变形记》和亚瑟王传奇,这一研究主题也是他一生治学的重点。在当时他与著名的民俗学者安德鲁·兰 (Andrew Lang)堪称齐名,还担任过美国民俗学会的主席;后来,他的研究超越了操英语的语言传统,广泛涉略到了古挪威、芬兰、俄罗斯,甚至日本的口头文学与民俗。蔡尔德在哈佛图书馆创立的“口头传承特藏”也在他的手上扩大了三倍,收藏超过20,000 册。
蔡尔德和基特里奇各自的学生中都有许多人一直在从事口头传统的研究和教学,不论是留在哈佛校内的,还是毕业后去了别的大学。这里我们无法再具体去展开了。但应当提到的是哈佛宗教俱乐部(the Harvard Religions Club)。大约从1899年开始,基特里奇与他几位同道就成了这个非官方俱乐部的忠实成员,大家每个月有一个晚上聚到一起,边吃饭边聊说彼此在宗教研究方面的话题。后来,俱乐部另一位早期成员穆尔(C. H. Moore)与其古典学同道杰克逊(C. N. Jackson)一道提出的动议,将米尔曼·帕里引入了哈佛古典学系。作为哈佛口头传统研究的第三代学者,帕里正是继承和发展蔡尔德与基特里奇精神遗产和学术传统的关键人物。
蔡尔德1849年首次到欧洲旅行便结识了格林兄弟,并在柏林大学听他们的讲座;德国语文学和古典学遗产是其在柏林滞留两年的研究主题,同时也是他在哥廷根大学听讲座的主要动因。格林兄弟高度关注中世纪文献、历史语言学、法律史、比较神话学和口头传承,与他们的知遇之交是蔡尔德从古典学走向口头文学研究的重要契机。80年之后,年轻的帕里到了巴黎的索邦大学专攻语文学,投师的正是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的精神追随者、历史语言学家和印欧语专家安托万·梅耶(Antoine Meillet),也正是在梅耶那里他了解到了中亚和南斯拉夫的活形态口传史诗及其民族志调查报告(拉德洛夫和穆尔库)。所以说,这样两位中坚人物先后问学浪漫主义运动余波袅绕的欧洲,从个人经历和学术渊源上来讲,他们既跟语文学,跟早期的历史语言学这样一个古典学传统不可或分,也跟当时关注民间传统、关注口头传承的人类学田野作业及其民族志成果有关。帕里基于荷马史诗的口头诗学阐释,后来有了弟子洛德的加盟和接续,洛德再传就传到了现在哈佛的第五代学者,以纳吉为代表……归总起来说,哈佛五代学者所坚守的口头传统研究塑造了哈佛的口头诗学实践及其内在理路,在跨学科的口头传统研究领域中竖起了一道道探索人类表达文化之根的标杆,可谓影响深远。口头诗学的理论性拓展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一方面,直接引导了20世纪民俗学三大学派的诞生:“口头程式理论”(也就是“帕里-洛德学说”)、“演述理论”和“民族志诗学”,另一方面,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潮形成也与此相关:“帕里-洛德学说”引发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口承-书写大论战。这是一个关于人类知识智力,包括逻辑乃至民主进程这样的一场涉及面特别广的大论战,整个人文学术界都卷入其间,其余波一直延宕至今,可见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古典学和希腊文化研究的范畴,对历史语言学、比较文学、民俗学、人类学乃至语言哲学、思想史、文化研究、书写研究等领域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中国史诗研究,乃至对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学术转型和范式转换也形成了不可低估的推力作用。
在“哈佛传统”尤其是“口头程式理论”的影响下,我们国内的史诗研究在整体上也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学术转型,也就是说从书面范式走向口头范式,从基于作家文学的“目治”模式走向了基于口头演述及其音声表达的“耳治”之学(郑重声明:“目治”与“耳治”之别来源于恩师静闻,而非我等的发明或创造)。比如说,我们的研究开始走向田野,开始超越集体性,开始关注个体──歌手或演述人,关注叙事传统、演述事件与受众、社区、传承人及其家族等之间的生成关系,在这样一些特定的社会情境里发现和阐释文本与语境之间的深刻联系,出现了一批来自田野实证的研究成果,并且在学理上和方法论上有所抽绎,有所建构,也有所突破。
说到“古典西学在中国”,我还想讲一点,就是说我们本土的史诗研究对荷马史诗研究会有一些什么贡献?甚或说对世界史诗研究,比如说印度大史诗,能够形成某种融通的视野吗?通过我们现在的一些田野案例,通过我们多民族、活形态的史诗传统和口头实践,我们的研究应当有助于解答“荷马诸问题”中的一些悬疑。比如说,荷马史诗文本是怎样形成的?根据哈佛古典学者纳吉提出一个文本演进模型,荷马史诗的发展经历过“五个时代”,长达两千多年,其间有一个最关键的时期是公元前6世纪,当时的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os)及其两个儿子正是通过泛雅典娜赛会来规制荷马史诗的演述本的。我们现在其实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当然性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有的学者现在把藏族《格萨尔》史诗做成精选本,里面把安多方言、康巴方言都糅合在一个本子里头,实际上这些方言对不同地区的民众来说,互相之间是读不懂的。那么这个文本化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回应了荷马史诗为什么杂糅着各地方言的疑问,其间有雅典僭主家族对史诗的一个政治攫用,但在背后实际上也有一种城邦意志。我们有的学者在做汇编本、精选本这样“格式化”的文本,抢救、整理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国家行为,是在意识形态的参与下来完成的。这样一种精选本的政治意义与学术意义不能并置。我们甚或可以想象,过多少年以后,人们再来看这个精选本的时候,是不是也会遇到荷马史诗当年遇到的一些无法解答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必须重新来审视这样一种精选本的制作过程,也就产生了文本制作及其研究必须要重新“回到田野”,并以口头演述为中心来制作我们的民俗学文本,我们叫科学资料本。由此我们提出“五个在场要素”必须同时在场:传统必须在场,演述者必须在场,传统受众必须在场,演述事件必须在场,还有研究者本人也必须在场,这五个“在场”要素同时在场的情况下,录制和誊写下来的文本,才是我们称之为民俗学学科意义上的口头文本。印度大史诗也有汇编和编订的一个漫长过程,我们诸多的活形态口传史诗怎样进入文本,怎样被写定,怎样被呈现,也从若干不同的面相映射着书面史诗的定型乃至被僵固的过程,从而也提醒我们要更多地关注史诗传统那气韵生动的口头演述及其生命活力的延续。因此,今天在古典学与口头诗学之间的学术轨辙上回顾“哈佛传统”的赓续及其多向性的对话精神,我们应当进一步反思中国史诗学自身的问题,回应本土史诗传承乃至人文传统所面临的现实遭际。
【发言人补记】由于时间的关系,有一些关键点在发言中未能展开,幸而白钢在会上的回应中有一段关键性的补充。如果编辑同意刊发,这里将“口头程式理论”的一个概述附上,以衔接“哈佛传统”与中国史诗学的学术转型之间应该涉及的某些知识点,以供读者参考。
口头程式理论(Oral-Formulaic Theory),20世纪美国民俗学重要的理论流派之一,又称“帕里─洛德学说”(The Parry-Lord Theory of Oral Composition)。大多数民俗学理论和方法都肇始于19世纪。相形之下,“口头程式理论”则是在20世纪中发展起来的寥寥可数的几种民俗学理论之一。这一学说的出现,既是对年深月久的“荷马问题”(Homeric Questions)作出的当代回答,也是通过实证研究和比较方法解决现实学术问题的理论范型。
在20世纪初叶,一位名叫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的年轻古典学学者,对千百年来令历代学者争论不休的荷马史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试图去解开“谁是荷马?他是怎样创作出被我们称之为荷马史诗的作品的?”正是这一被叫学界称为“荷马问题”的千古悬疑,引发长达几个世纪的学术争论。因为在所谓“荷马时代”稍后不久的年月里,这个问题就变得模糊起来――没有关于荷马史诗创作者的确切记载。学者们只好根据零星的线索,作各式各样的推断。这些见解,又粗略地构成了被称之为“分辨派”(unitarians)和“统一派”(analysts)的两个彼此对立的阵营,通俗一点说,就是“荷马多人说”和“荷马一人说”。双方都以为自己掌握了有力的证据,后来却又都发现他们难以驳倒对方。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至关重要的新材料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学术探索走进了死胡同,长久地徘徊不前。应该出现一种全新的思路,以突破以往研究的格局,在继承前辈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独辟蹊径,以创新说。
帕里承担起了创立新学说的重任。作为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古典学者,他曾深受法国历史语言学的影响,对19世纪德国语文学的成就也极有心得。梅耶的比较方法,艾林特、顿泽和其他一些人对荷马修辞和步格的深入研究,使他获益非浅。大约在同时,拉德洛夫和其他学者关于突厥和南斯拉夫的民族志报告,又使他对活形态的口头史诗演唱传统有了一定的了解。不过那时他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在他的古典文学研究与活形态的史诗演唱传统之间的关联。他从分析荷马史诗中固定出现的“特性形容修饰语”(如飞毛腿阿基琉斯,灰眼睛的雅典娜,绿色的恐惧,玫瑰指的黎明等等)及其复现频率入手,很快就发现,荷马史诗的演唱风格是高度程式化的,而这种程式来自悠久的传统。荷马史诗是程式的,也就必定是传统的。随后,他又发现,这种传统的史诗演唱,只能是口头的。不过这些还只是以语文学分析为基础的学术推想,怎么才能印证它呢?帕里得知,在南斯拉夫地区当时还存在有口传史诗的演唱传统,他于是决定去那里进行田野作业,以求通过对口头史诗演唱进行近距离的观察和比较研究,发现口头文学活动的基本特征。他的学生和助手艾伯特·洛德(Albert Lord)参与了调查活动,这又成就了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这师徒二人共同创立了“帕里-洛德理论”,或者叫“口头程式理论”。在南斯拉夫的调查,主要在六个地区里进行,其收获是巨大的――他们通过与南斯拉夫的活形态的口头传统作对照和类比研究,确证了他们关于荷马史诗源于口头传统的推断,并进而印证了他们关于口头史诗创作规律的总结。在这次历时近两年的田野作业期间,他们用口述的文字记录和特制的声学录音装置采集了大量史诗演唱,从而构成了今天哈佛大学威德纳图书馆“帕里口头文学特藏”(The Parry Collection of Oral Literature)的主要内容,这次实地调查及其成果随后成为世界上少数搜集和收藏口头演唱活动的成功范例。
口头程式理论的精髓,可以概括为三个结构性单元的概念:程式(formula)、主题或典型场景(theme or typical scene),以及故事范型或故事类型(story-pattern or tale-type),它们构成了口头程式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凭借着这几个概念和相关的文本分析模型,帕里和洛德很好地解释了那些杰出的口头诗人何以能够演述成千上万的诗行,何以具有流畅的现场创作能力的问题。由于这一理论的创立起因之一,主要是对古老的“荷马史诗”文本进行当代解读,这就不能不打上一道鲜明的烙印,并成为分析和阐释那些已经由文字固定下来的史诗文本(以《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为代表,还有被经常提起的《贝奥武甫》《尼贝龙根之歌》《熙德之歌》等)的利器,从史诗文本中发现程式和分析程式的频密度、分析句法的结构(如平行式、跨行、韵律特征等等)、解析主题和典型场景,都能驾轻就熟,具有明显的普适性和较强的阐释力。此外,语文学和人类学,是在帕里之前早就存在了的学科,但将它们结合起来,以对口头演述中的若干核心要素进行深入的把握,则是由帕里和洛德首倡的。这一套新的学术工作原则,就既体现出了语文学的严谨和精细分解,又具有人类学的注重实证性作业,注重田野的特征。分析性工作与实证性工作,在这里获得了绝妙的统一。该理论的两位创始人具有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素养,两人专擅的方面有一定的差异,加之帕里在初创学理不久即去世,这就为该理论带来某些特色,例如它的草创和后期发展之间的跨度比较大,它的理论体系具有相对开放的性质,它的普适性和广泛的影响,又反过来带给它活力和巨大的发展空间。从精神特征上看,帕里-洛德理论与上个世纪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中试图重建历史和偏重历时性研究的偏好有明显的关联,同时又是形式主义和结构研究的某种接续。在后来的发展中,它一方面影响了近年势头颇健的“演述理论”(Theory of Performance)和“民族志诗学”(Ethnopoetics)等学派,另一方面又广泛地影响了区域文化研究和各种口承文化传统的研究。
国外民俗学界关于口头艺术(Verbal arts)与“文本”研究的激烈讨论与近年来十分活跃的“演述理论”及其对文本意义的发掘关系密切。而“演述理论”即是与早期更偏重于文本分析的“口头程式理论”有一定亲缘关系,并在文本概念的全新界定上直接受到了“帕里─洛德学说”的启发,即真正的口头诗歌文本是“演述中的创作”(Composition in Performance),“诗即是歌”,“每一次演述都是一次创作”。由于演述涉及演述者和观众,正是二者的互动作用才产生了“文本”;因而“文本”的概念来自于“演述中的创作”。这正是口头程式理论关于“文本”的概念,是在口头创作形态学的意义上被界定的,这显然区别于后结构主义的“本文”概念。从文本概念的界定到口头诗学的文本研究之间,口头程式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在基本架构上利用语文学、语用学和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以史诗文本的语言学解析为基础,论证口头诗歌尤其是史诗的口头叙事艺术、传统作诗法和美学特征。因而,口头程式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口头诗歌的创作理论。作为口头诗学(Oral Poetics),它是立足于口头传统本身对西方古典诗学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反拨,总体上而言,先后纳入口头史诗研究视野的文本对象和范围,随着田野观察的发现而不断得到拓展,其间也有其历史性的发展和变化。
自这一学派的扛鼎之作,即洛德的《故事的歌手》(Singer of Tales)于1960年面世以来,其理论成果和工作方法,超越了古典学、斯拉夫研究,甚至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科边界,已成功地应用到了多达150种语言传统的学术阐释中。另外,帕里─洛德学说与晚近才发展起来的重视非精英文化、非主流文化的人文思潮有某种契合关系,因而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美国民俗学的发展轨迹,并且成为西方知识界“口承─书写大分野”(The Great Divide Between Orality and Literacy)这一文化论争的先声,为传播学、书写研究、文化研究等领域带来了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
有关口头程式理论的基本学科规范和主要内容,读者可以从约翰·迈尔斯·弗里的《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朝戈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获得,其中列出了直到1982年为止的相关学术成果及其注释,在该书所择选的1800余个条目中有足足1500条直接成长于帕里和洛德的工作成果之上,由此可见这一理论的国际学术影响是空前的。此外,读者还可以重点参阅这一理论的奠基之作《故事的歌手》(尹虎彬译,中华书局2004年版),它不仅使“口头程式理论”成为一种方法论,而且使口头诗学逐渐成为一门学科,因而一直被誉为口头传统研究领域的“圣经”之作。
(朝戈金 巴莫曲布嫫 撰编,摘要以关键词形式发表于《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6期)相关阅读:
- 《故事的歌手》漫议 (admin, 2008-8-25)
- [程志敏]谁杀死了荷马? (admin, 2008-8-25)
- 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 (朝戈金, 2008-8-26)
- 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 (朝戈金, 2008-8-26)
- 口传史诗的误读 (朝戈金, 2008-8-26)
- 朝戈金的《口传史诗诗学》 (施爱东, 2008-9-13)
- [程志敏]谁杀死了荷马? (放牛班的课堂, 2008-9-13)
- 口头诗学问题——文艺研究笔谈 (朝戈金, 2008-9-18)
标题搜索
日历
|
|||||||||
| 日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
| 1 | 2 | 3 | 4 | 5 | 6 | ||||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
| 28 | 29 | 30 | |||||||
我的存档
数据统计
- 访问量: 317865
- 日志数: 177
- 图片数: 21
- 影音数: 23
- 文件数: 8
- 书签数: 27
- 建立时间: 2008-07-21
- 更新时间: 2014-08-19